
河北赵县范庄二月二龙牌会现场。

民国进香的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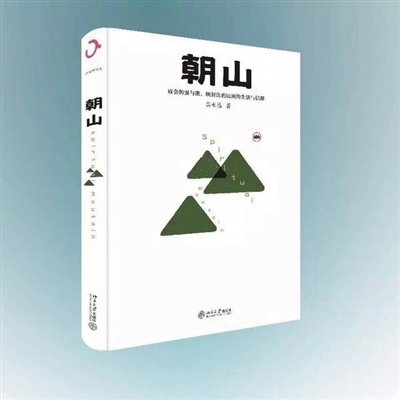
《朝山》
作者:岳永逸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以北京妙峰山和河北苍岩山庙会为个案,综合旧京庙会的记载,形成自己庙会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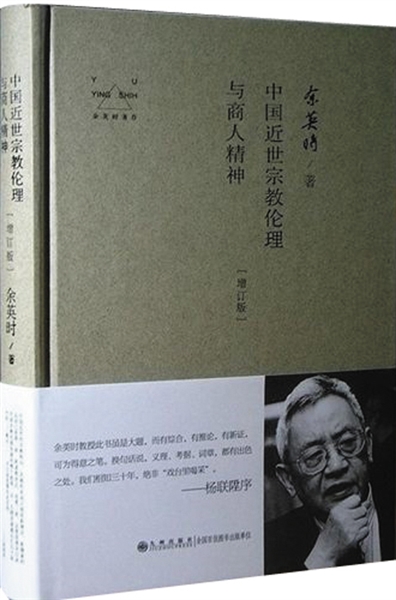

岳永逸 四川剑阁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活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 2016年冬,朋友圈里关于乡土宗教的段子似乎突然多了起来,先是有人说河南某教堂在圣诞夜唱梆子做弥撒,随后又因台湾摄影师沈昭良的作品,引发网友“揭发”中国各地的灵堂酒会、送葬蹦迪、祭祖歌会,接着陕西“血社火”与各地庙会的图片又随着年关将近而逐渐增多。 对于这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宗教活动,大V们称之为“中国化宗教先进典型”者有之,说应该“移风易俗”,甚至直接斥为“地下邪教”的人也不少,比较带有学术意味的讨论,也总在“中华文化”的大命题下做文章。 但是,这些乡土宗教的实践者与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这类活动如何能在政治权力、精英话语与媒体奇观的夹缝中延续至今?那些表面或怪异或土气或可笑的祭拜,能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底层人民带来怎样的情感体验与信仰感悟?在媒体一波一波的热点冲刷之后,这些问题似乎没人提起,或者没人记得。也许不能全怪互联网上的阅读者,对乡土宗教长期的污名化,使得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思考,或者被禁止思考这些问题。而当我们重新开始思考时,又“受官民和中西二元对立话语的规训,并以基督教等制度性宗教为高级宗教”,在西方话语框架下,自觉不自觉地让中国的乡土宗教处于劣等的位置。 被贬低和打扮的乡土宗教 岳永逸这本《朝山》以及其中所提出的“让渡性的乡土宗教”的概念,不仅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了庙会被禁止与被污名化的过程,以及复兴之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则,也站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将整个华北平原的人文地理学纳入视野,描绘出城乡内外的朝山庙会如“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景观。 它不仅告诉我们,今天人们看待乡土宗教的眼光中有多少偏见来自于政治的遗产,也告诉我们当下红红火火的“香火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之中,又有多少小民的智慧、反抗的策略与“层垒”的话语。它让我们看到,乡土宗教如何在大历史的洪流中砥砺生存,如何在香火的聚散流转中形成神州图景,也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朋友圈中看到上述新闻时所发的“高谈宏论”,因了什么的名?顺了谁人的意?又从了何等的力? 在中国,“宗教”与“乡土宗教”的命运不尽相同,当康有为建孔教会、章太炎要佛教兴国时,乡土宗教却从来都被扫入“迷信”、“落后”、“愚昧”之列。进步知识分子要“德先生、赛先生”,务实知识分子只谈庙会的经济性、庙产办学的教育性。正因从晚清开始,庙会就是被改造和被禁止的对象,所以在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后,20世纪末中国庙会的复兴才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但正如岳永逸在书中用妙峰山和苍岩山两个圣山庙会的例子所描述的,乡土宗教的复兴不是因为它被正名,而首先是因为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符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纲领才能获得生存空间,随后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转而成为“圣山景观”,近年来还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而“由俗入礼”。 复兴本就借了经济、政治与非遗的名义,于是出现“被承包的信仰”或“香火经济”是再自然不过了。而反观旁观者的眼光,蔑视与俯视仍居主流:在媒体是视之为利欲熏心的典型、口诛笔伐的对象,在网络社区是惊呼“怪异!愚昧!可笑!”,在知识圈是民俗研究中功利主义和功能论的盛行,其本质原因,是因为我们总要用别的“名义”,来判断乡土宗教的价值,乃至决定它的生死。 流动的灵力:离地三尺有神明 乡土宗教在复兴过程中借了他人名义,因此圣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景区,但与此同时,乡土宗教本身也有了事实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庙会再次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和自我表演的剧场。在《朝山》一书中,我们看到,乞丐、香头(巫师)、香会会首、民间艺人、农民、工人、游客、承包殿堂的庙主、大小资本家、地方政府、知识精英、媒体、形形色色的人都会聚于圣山之上,他们的目的、观念、话语全都各自不同,圣山上的神灵也随他们所需而各种“排列组合”,统一且固定的圣地认同并不存在,每个人参与宗教的方式也殊为相异。正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的参与,在不同层面上影响到庙会的生态与形态,因此圣山与庙会也就被叠加进多重意涵,“反过来,被人们持续层累的妙峰山也就成为社会演进的一面棱镜。”尤其是在妙峰山景区化的当下,“以旅游观光为目的的上山者日渐增多,这些新增加的参与群体更感兴趣的是妙峰山这座山,而非灵感宫中的老娘娘”,如此,怎能认为聚散之中的圣山与庙会就代表一种文化、诉说一个故事、承载一种心意? 《朝山》沿用他以前使用的“让渡”一词作为关键概念,“让渡”一词指的是香火的灵力可以流转聚散,呈现出一种“自流体”的性质,可以在圣地与村居、圣地与圣地之间流转,丫髻山与妙峰山之间似乎有一条香火互通的走廊,当一方衰落时,另一方却隐然而旺。苍岩山与它周边大大小小的庙会之间也有这样的灵气通道,有时祭神的香火聚于圣山之顶,有时散开藏入平原。随着灵气的流转,各类物品也随之翻转,于是“山里山外的不同参与者的财富、资本被再度分配”。 在这里,神来自于人并归于人,礼与俗也无法根本区分,当妙峰山香会由“皇会”向非遗变脸、转化的同时,在苍岩山,传统敕封的“礼”实现了向文物、非遗等现代之“礼”的转化,乃至杨开慧也从红色叙事中脱胎换骨,成为三皇姑身边新的“圣母”。在庙会逻辑中,通过妥协与分享,凡夫俗子与神灵之间达成共识、地方政府与庙主实现双赢、神灵、信众、政府与民族国家共同分享“信仰承包”所带来的地方活力。最重要的是,正因人与神、礼与俗、制度与民俗可以相互交替转化,聚与散的庙会赖以存在的中国大地,其空间本身也具有“自流体”的性质。家、街、城、乡土,因为其深层上的同构性而可以部分地相互转化,中国社会因此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神州”——那“离地三尺有神明”的生活大地,本质上就是以神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整体性关系的世界,城市乡村概莫能外。 因为有神,所以人成为了人,当我们把神从人的世界中剥离后,人就成了物。作为《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以及《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的姊妹篇,《朝山:庙会的聚与散》是迄今为止华北庙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与前两本书(尤其是《行好》一部)着力于微观深描略有不同,随着问题意识的集中与笔力的深入,《朝山》一书更倾向于站在中观的半空,既立足时间之河的当下回望上游,也将整个华北平原的人文地理学纳入视野。当我们一次次在乡土宗教的媒体奇观中满足猎奇心或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时,这本书中严肃的民俗学分析也许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立足之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村志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